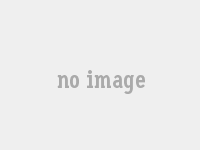袁香芹,南都观察“未来的事”特约体验官
几乎每个基金会的故事都是从“发钱”开始的,因为最开始只有钱。
游劢记得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恒申基金会”)在2013年刚成立时,也不太清楚要做什么,只是发现儿童青少年、养老、扶贫这些领域已经有很多关注了,而妇女领域似乎还缺一点,恒申基金会就开始给贫困妇女发生活补助金。
只有钱,人力有限,去哪里找那么多贫困妇女发钱?恒生基金会秘书长游劢和同事们求助一些更有经验的公益从业者,得到最多的建议是联系各县市的志愿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多由本县的志愿者组成,熟悉本县甚至下辖各镇、各村的情况。基金会把资助标准告诉这些县域组织,他们能找到那些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女性。
▲ 2017年5月,福建龙岩上杭县,当地的阳光公益协会的志愿者“带着福建恒申慈善基金会的温暖,分别给三户贫困母亲每户送去慰问金二千元”。 上杭县阳光公益协会
这过程中又出现新问题。游劢说:“他们都很认真负责,信息审核、补助金签收、拍照……做得非常好。但他们没有稳定的项目,大多都是志愿者,人员也不稳定,可能做着做着就不做了。”调查、走访、日常办公……都需要开支,志愿者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很容易受行政费用不稳定的影响,它们本可以成为基金会资金流动的重要路径,但道路常常中断。
“没有钱(支持机构的运营),就招不到人。人员不稳定,就没有稳定的项目。志愿服务做得不专业,就没有一定的影响力,政府(采购志愿服务)、公众(捐款)不了解你,也不会信任你。最后就会变得根本没有资源,成一个死循环。”基金会需要和更一线的专业组织合作,使善款实现更积极、高效的社会影响,但在和县域组织合作的过程中,游劢发现他们非常不容易:“如果基金会不去做一点事情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发展起来。”
恒生基金会调整了资助形式,不仅向县域组织提供要发放给贫困妇女的补助金,还另有一笔“执行经费”,优先用于补助金发放的行政开支,但是如果还有剩余的话,第二年就转变成志愿者组织非定向(不限定在某一特定项目)的资助款,可以用在学习、培训等等有利于机构发展的事项上。
在关注妇女的领域上做久了,恒申基金会开始寻找同领域的其他机构,也许除了直接发钱之外,其他机构有更多形式的支持项目。恒申基金会希望通过资助机构的形式来提高各机构的专业性,以更好的支持受助对象。先把道路、加油站、服务站这些基础设施建好,就不用担心突然的中断了。
慢慢的,一些四处分散的机构和断断续续的行动开始变得有序,“(这些机构)得到资助之后,开始以一个个项目的形式去工作。如果没有资助支持,一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改变、提高。”游劢开始理解“行业支持”这个概念更深的内涵了。
▌作为“资源上游”的基金会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量的公益基金会成立、壮大,资中筠称其“开创了诸多事业,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其他非营利机构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类”。
▲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早期入华的美国基金会,1921年,其支持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图为落成典礼上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的合影。 rockefellerfoundation.org
1981年,“中国儿基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并施行,民间涌现出大量的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7300家基金会。
作为公益领域的“资源上游”,基金会聚集了包括资金在内的众多社会资源,也因为资源的再分配而被关注、讨论甚至批评。2016年开始实施的《慈善法》则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目前大多数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形式是基金会。
相当程度上,基金会离捐赠资源更近,相比一线的“草根机构”,在整合社会资源、研究社会问题方面也有更专业的能力。许多公益从业者认为基金会应该把募集的社会资源资助给一线组织,因为后者离社会问题、受助对象更近,更了解来自一线的需求和问题的解决路径。
如果以“资金的使用”分类,纯粹将募集的善款用于资助更为一线的公益组织的基金会称为“资助型基金会”;将善款直接投入项目运作,自己寻找受助对象或社会问题,并研发公益项目予以帮助、解决的基金会称为“运作型基金会”;也有既资助也运作的基金会。
据2018年《中国基金会评价榜》的发起者李志艳推测,中国实际上做资助的基金会可能就150家左右,占当时全国基金会数量的2%左右。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说,德国有2万多家基金会,大概只有30%是运作型的,美国约9万家基金会中,运作型的不超过4%。在欧美这些国家,“如果基金会要自己做项目,要先说明原因——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可以关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NGO了”。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志云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曾指出,中国资助型的基金会在整个基金会行业中的占比太小,不利于基金会作为整个公益行业的有机组成去推动行业的发展。因为合理的分工、充分的协作,可能更有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王志云说:“基金会作为‘财团法人’,本身就具有整合、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是基金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专业。没有这样的一种专业分工和协作,我们(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态。”
▲ 为了促进中国与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民间组织之间的友好对话,德国的墨卡托基金会在中国开展了“国家与社会-中国未来合作伙伴”主题项目,其中一项为支持中国的基金会秘书长前往欧洲参访交流,促进双方的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图为“访欧团”成员在斯图加特了解当地社区基金会的项目。 CFF2008
▌建立一个怎样的“生态”?
2018年,游劢分析过福建当时的全部339家基金会,按地域分布,数量前三的分别是福州、泉州、厦门,基本上涵盖了福建经济最好的三个区域。推测其中108家是由企业出资成立的。“但是真正活跃的基金会根本没有几家。”
游劢认为活跃的基金会应该“针对所关注的领域或者议题,有相对稳定的项目常年开展,并被当地的民间组织所熟知,还能与之产生互动”。他说:“特别是‘被当地的民间组织所熟知’这一点,(基金会)要能与之产生互动,可以是资助的形式,或者是大家共同参加行业内的培训、交流。”
根据这一标准,游劢在福建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基金会,一起探索基金会如何在本省支持公益行业发展。包括林文镜基金会、正荣基金会、同心基金会等,几家基金会一起“凑钱”,支持公益行业从业者的学习培训、举办行业研讨、资助行业领域的发展研究报告……“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灵活的‘联合资助’的形式,花少钱,又能做很多的事情。”
核心又回到了县域的公益组织上,游劢说:“我们觉得公益行业在福建的发展,并不是看福州、厦门、泉州做得多好,而是一定要让县域的NGO起来。只有县域的起来了,整个公益生态、大的行业才能发展起来。”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是一位常年关注公益行业的研究者,她认为在公益领域,社会选择非常重要。这和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市场选择相似,“社会选择会给大家一个内生的动力,沿着‘社会效益更加’的路径前进。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激活更好的社会选择,让那些在县域的、一线的组织做的事能被看到。只有它们起来了、存活下来了,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良性循环。”卢玮静认为社会资源也存在一种漏斗效应,从省级城市到地市级、县域,资源层层下渗。但是“大家没有把太多的经历关注在扎根最基层的组织,而它们才是离受益对象最近的”。
关于“给钱”,公益领域已经有太多反思,但赋予公益组织独特性的并非资金,更重要的是独立于商业领域的专业服务。关于受助对象的改变,卢玮静说:“这其实非常需要专业的接触,面对面的服务。一旦基金会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会明白要支持更多的一线NGO。当一个基金会发现给钱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去思考如何把钱转化成专业的服务。这样才能改变受助对象的境况。但这个行业里目前最稀缺的就是专业、能力。”
▌为失败的成本买单
“在公益行业发展的初期,需要更多的组织愿意站起来为失败的成本买单。”卢玮静认为,虽然也有一些已经很成功、成熟的公益项目,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社会问题是复杂多变的,地域变化、时间推进,都会带来新的挑战,而进入到新的现场时,需要失败的成本。“你愿不愿意去陪伴那些在发展初期的机构,一起走过那么一段艰难的道路?陪伴它去经历失败、去摸索?因为可能只有经历了失败以后,才知道合适的道路在哪里。”
在基金会资助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的情况。受资助的组织认为自己是在为基金会做事,而基金会则认为自己只是资助了一笔钱给一个独立的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核心目标不明确,一线组织很容易为了完成项目计划书的硬性任务而偏离原本的工作方向,忘了自己原本的责任是去解决社会问题本身。
卢玮静认为责任主体的归位非常重要。“重点还是要NGO去关注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自己的专业性与核心竞争力。一棵树的成长不应该被带到另外的光的方向,而应该长在自己的主干上。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暂时的资源带偏,而是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
而在非指标导向的资助关系里,责任主体常常是回到了一线公益组织的身上。“这一点在资助领域非常重要,基金会不要通过资助关系来让NGO去走它所解读的‘基金会想要的方向’,这样可能会导致NGO走到一个跟社会问题、受助对象和机构发展有一定偏移的地方。”卢玮静说。